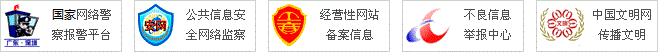切不可轻言填补空白
-雅言
顾炎武认为,“著书必前之所未尝有,后之所不可无”。这个标准很对,但要达到也很难。随着时代的进步,学者越发感到“我之所欲言,已出古人口;我之所欲书,已出古人手”。糟糕的是,有的学人自鸣得意的“新创”,其实早已是中外同行的“旧说”。
在近期央视《百家讲坛》上,某教授称:两千多年来被冠为“暴君”的商纣王属于历史最为悠久的“冤案”,复有媒体将其誉为“为纣王‘翻案’第一人”,这遭到多个学者的批评,为纣王“翻案”实是“自古就有”,可列举出的人物至少有子贡、孟子和现代的郭沫若。
在学术上,要避免自己的成果难以和前人相区别,“扎实”是最起码的要求。所谓“扎实”,用黄侃的话说,就是“扎硬寨,打死仗”。黄侃之所以成为大师,就在于他的治学精研,所治经、史、语言文字诸书皆反复读过多遍,其熟习程度至能举其篇、页、行数,十九无差误。他对于随便翻翻,点读数篇辄止者称为“杀书头”。“他做工夫的精神,绝不似实用主义者那样为写作一文只翻所需的材料,而不一字一句地读透会通全书的义理。”
如果对自己领域的基本著述没有通盘读过或只是囫囵吞枣地翻阅过,偏又喜好著书立说,便很容易弄出让人大跌眼镜的故事。刘心武1996年发表文章,曾将黄庭坚的名句“江湖夜雨十年灯”说成自己梦中得句,引发诸多非议。后来,他在自述中总结了教训:都是浮躁惹的祸。“拿到想读的书,心急火燎,好奇心驱使下,一目十行,匆匆翻页,颇似狼吞,亚赛虎咽。这种囫囵吞枣的读法,往往造成消化不良,储留在记忆里的,多是些碎片式的或模糊不清的印象。”而在写文章时,又习惯于“随手拈出一些往日阅读印象来,或举为例证,或涉笔成趣,有时来不及查书核对,便会马失前蹄,或张冠李戴,或乱点鸳鸯,闹出笑话,引出批评。”
好的学者,还对未知领域心存敬畏。“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这一说法,在古代,倒也不是瞎吹。因为那时所说的天下,并不很大,尤其是不包括外国。例如,孔子生活的年代,可供阅读的典籍就很少。根据来新夏的看法,那时节所谓“学富五车”,不过是读过五辆兽力双轮车装的竹简而已,文字量并不大。但今日的情况不大一样。知识、信息快速增长,任何人都绝无可能遍阅天下文献。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学术界的分工只能越来越细,知识分子只有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将研究领域日益窄化,才有可能真正熟悉已有的研究成果,并有所创新。
而时下,多有学者屡屡对学术界应有的分工妄加非议,又乐于越界到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争夺话语权,却偏能哗众取宠,这表明我国的知识生产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学者在对外公布自己的成果时,应斟酌再三。魏明伦有言,文章要硬写,即写不出也要写,但写完后切忌硬发,一定要等到多次修改后再拿出去发表。这是非常好的经验之谈。顾炎武在写好《日知录》后,迟迟不付梓。他的学生要求刊行,他说读书未遍,怕有与古人重复处,还需继续涉猎一些典籍。《日知录》终成享誉后世的名著,与顾炎武“该出手时才出手”有直接关系。
高估自己成果的价值,也是为学之大忌。纪晓岚素以博闻强记、遍观群书著称,但他一生除总持《四库全书》和撰写一部《阅微草堂笔记》外,没有什么令人瞩目的著作。据老辈人传说,他因为书读得太多,往往分不清哪是前人旧说旧事,哪是自己的新解新意,生怕有与古人“暗合”处而贻人口实,所以不敢多有著述。纪晓岚的做法,有些过,但他的担心,却也并非多余。因为人的记忆,毕竟有局限。
张宇燕是我国当代的经济学者,治学一向严谨,但也曾为记忆所误。他在几年前写的一篇文章中,为了说明经济状况迅速改善往往会引发社会动荡,特别引用了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论断:法国大革命的根源之一,在于法国农民受到的束缚大幅度减少,生活水准显著提高,而随着手铐的去除,剩下的脚镣往往会变得百倍的不能容忍。他在这篇文章中还给托克维尔这一见解“起了”一个名字:“托克维尔效应”。后来,张教授为了写一部关于美国的著作,又把多年前读过的一批书籍翻出来重温,其中包括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当张教授在该书中读到“人们可能受的苦减少了,但他们的敏感度提高了,这种现象现在通称为‘托克维尔效应’”,望着14年前曾经被自己用笔重重画过的、在旁边还加了惊叹号的这段文字,他感到非常震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后来,他专门著文检讨这段他所谓的“丢人现眼,无地自容”的经历,得出一个重要的心得:“切不可轻言填补空白或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