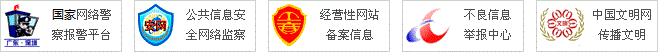谈论“文化保守主义”,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文化”?如何去“保守”?
这里我不想陷入繁琐的定义讨论。我们现在讨论“文化”,一般都是把它当作民族性、即一民族不同于它民族的那些特征而言,即所谓“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西方文化”之类,而不同于改革前意识形态那种把“文化”看成超民族的与特定制度对应的“上层建筑”(如所谓“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之类)。同时,这种文化或民族性主要并不指那些客观的生理差异(如中国人之黑发黄肤和西欧人的金发白肤等),而是指主观的价值偏好:例如按照流行的说法,在“形而下”层面,中国人喜食米饭,西方人喜食面包,是为“饮食文化”之别;在“形而中”层面,中国人重德,西方人重才,是为“伦理文化”之别;在形而上层面,中国人长于综合、形象思维,西方人长于分析、逻辑思维,是为“最根本的”或“深层的”文化之别;等等。不管这些说法是否准确,不管你对这些假定的或确实存在的偏好如何褒贬——不管你主张中优西劣还是西优中劣或者各有千秋,所谓“文化”的区别被认为是价值偏好的区别大概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问题在于:一个人的价值偏好好说,一个民族的价值偏好如何确定呢?中国人张三重德,西方人约翰重才,这就能说明“中国人”重德而“西方人”重才吗?有多少中国人像张三这样偏好,又有多少西方人像约翰这样偏好?张三或约翰能“代表”他们各自的“民族”和“文化”吗?
如果说以上问题还可以通过统计来解决,那么更麻烦的是:你怎么能判定这些人有同等的可能来表达自己的偏好?举个极端的例子: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与曼哈顿的犹太人行为方式有如天壤之别,你能说他们体现的是两种“文化”吗?你能根据前者说“犹太文化”特征是服从忍耐逆来顺受,或根据后者说犹太文化特征是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奥斯威辛里的犹太人与波兰人行为相似,你能据此说“犹太文化”与“波兰文化”很相似吗?
显然,根据常识我们只能说:犹太人在奥斯威辛与在曼哈顿的行为(乃至思维)迴异,这不是“文化”之别,而是制度之别。犹太人在奥斯威辛处于奴隶(或者说连奴隶都不如)状态,而在曼哈顿处于自由中,两者的“区别”不过如此。在奥斯威辛我们是无法判断犹太人与波兰人有何“文化”差异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表达价值偏好的自由。而在曼哈顿,如果犹太人与波兰人行为存在着具有统计意义的集体差异,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犹太文化”与“波兰文化”的区别何在了。
奥斯威辛与曼哈顿的差异也许太极端,但不那么极端的差异也能导出类似的逻辑。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举例说:“我喜欢吃米饭和你喜欢吃面包是文化之别,但我被要求吃米饭和你喜欢吃面包,就决不是文化之别。喜欢缠足和喜欢隆乳,是文化之别,但强迫别人缠足和自己喜欢隆乳,就决不是文化之别。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儒教是文化之别,但信仰自由和异端审判决不是文化之别。喜欢拥戴大贤大德和喜欢拥戴大智大能,是文化之别,但统治者的权力是否来源于被统治者的授予(即来源于后者的‘喜欢’),就决不是文化之别。”
问题的关键在于:价值偏好是人的大脑评价的,而大脑每个人都有一个,这一点普天下皆同。某个民族是一人一脑,而另一民族却是“共脑人”——哪有这回事?所以一个民族如果有不同于其它民族的特殊价值偏好,这不是因为这个民族的成员共用了一个大脑,而这个大脑的构造与别的民族有什么区别,而是因为(由于历史、环境等原因)这个民族的每个人,或至少是大多数人各自都有某些价值偏好(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在形而上层面),而这些偏好恰好又有共同之处。换言之,“民族偏好”是其每个成员个人偏好的“最大公约数”。如果每人的偏好不能充分表达,“最大公约数”也无从统计。这样我们连“某某文化”是什么都无从说起,更别说比较优劣和假如优的话又如何“保守”它了。
例如有些人说:西方人尚能,而中国人尚贤。我们怎么证实或证伪这个说法呢?当然不是凭某个中国人(或西方人)写过一本鼓吹尚贤(或尚能)的书,——这样的书和相反偏好的书在很多民族中都会有人写,也不是凭某个民族的当权者是否把这本书挂在嘴边,而只能是看生活中一个个具体的人是否确实表现了这些偏好。尤其在与他民族比较时,更只有在可比场境下才能体现这种差别。假如同样在自由的选举中,一个民族的选民偏好于选择贤而未必能的人物,另一个民族的选民偏好于选择能而未必贤的人,这种“文化差异”就得到了证实。甚至如果当选者自称己贤而其实未必,你可以说选民受骗了(因此下次不会选他),却不能否定这种“文化”的存在,因为的确是这种偏好使他当选
但如果一个民族自由选举出了能者,而另一个民族的“贤者”却是强权自封的,那么即便后者是真贤,你也不能说这里有什么“文化差异”——因为他的上台与人们的“偏好”并无关系。你只能说这里有“制度”之别,却不能以此证明什么“文化”之别。中国历史上的帝王无不自称贤明,这并不能证明“中国文化”尚贤,正如明清之际大儒们多有“凡帝王者皆贼也”之论,这也不能证明“中国文化”不尚贤一样。
可见,一种“文化”是否尚贤,关键是看这种“文化”中的一个个活人是否自由地表达出“尚贤”的偏好。
同样,一种文化是否崇孝,也要看这种文化中的一个个人在没有父权强制的状态下是否能孝敬父母。当年五四时代一些人攻击启蒙者“讨父仇孝”,毁灭中国文化,陈独秀答道:“我们不主张为人父母翁姑的专拿孝的名义来无理压迫子女儿媳的正当行为,却不曾反对子女儿媳孝敬父母翁姑, 更不说孝是万恶之首,要去仇他。” 这道理本是显而易见的:真正的孝敬决不是父权压迫出来的。如果只有在“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的威胁下儿子才会孝敬父亲,没了这个威胁他就会忤逆胡为,能说这是真的孝子?如果一个民族中这样的儿子占到某种比例,能说这个民族的“文化”是崇孝的?
可见对于那种指责在逻辑上只能有两个评价:如果中国人真有崇孝的文化,过分严厉的父权没有又何妨?怎么能说否定这种父权就是毁灭了崇孝文化?而如果没有严厉的父权人们就会不孝,那所谓崇孝文化是否真的存在过就很值得怀疑,又谈何“保守”或毁灭呢?
当然,真正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时代的民间父权是否严厉到陈独秀们当时认为的那个程度?专制国家能允许“为父绝君”的原始儒家伦理存在吗?如果以“国族权益”取消了家族权益,会不会等于君权取消了父权,陈独秀所期望的自由在那种情况下能成长起来吗?
所以,正如真正的爱情决不是“强扭的瓜”所能产生的一样,一切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在它能够凝聚人心以抵制外部之强制同化的同时,也决不需要在自己内部搞强制同化。而所谓“保守”文化,或者说捍卫文化,就是要反对强制同化,而不是要强制反同化。恰恰相反,文化的捍卫者,必然是强制的反对者,即那些既反对强制同化,也反对强制反同化的人。
事实上我们的文化中本来就有“和而不同”这个古训,遗憾的是现在有些人只用这个概念来强调各种文化之间的多元共存关系,却不愿在我们这个文化内部实行这一原则。其实,这个古训在我们的先人那里倒确实是就个人之间的价值多元而言的。古代先贤在“华夷之辨”这类文化间问题上一般都主张以华化夷,很少人有华夷价值平等的主张。“和而不同”本是主张华夏内部各种学派、思潮、观点和价值偏好应当“各美其美”,真正爱好中国文化的人不会不知道这一点!
在自由发展状态下,文化差异是不可能也不应当被消灭、甚至可能不会缩小的。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奥斯威辛与曼哈顿也许是难免严重冲突的。但“文化”的差异真的会引起严重冲突吗?根据上面讨论文化差异的逻辑,有人提出了这样的命题:
“在可以实证的意义上,世上哪两个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最大?是美国与穆斯林国家?是西方与苏俄?是中国和美国?都不是,‘文化’差异最大的两个民族,就是美国和瑞典”。
这个命题的根据是:正是在大致相同的自由表达与民主选举机制下,美国人与瑞典人表现出了相差最远的两种价值偏好:美国人选择了一个相对而言最“自由放任”的体制,而瑞典人选择了一个“从摇篮到坟墓”都依靠国家安排的机制。
不错,也许例如前苏联的机制与美国或瑞典的机制相比差异也很大,甚至超过美瑞之差异。但是,问题在于俄国人的机制并不是他们自由选择的(当允许选择的时候,他们就选择了另外的机制),而美国人与瑞典人的机制是他们各自选择的。因此美瑞的差异的确是两国人民价值观与选择偏好的差异,或者说是“文化差异”,而俄罗斯人与美瑞两国人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能否选择”的差异而非“选择什么”的差异,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价值观差异或曰文化差异无关。只能说俄国与美瑞两国的制度差异都很大,至于他们的“文化差异”如何,根本无法判断。
然而,尽管当今美国与瑞典的利益可能远非一致,但是没有任何严肃的人会设想这两国或两族在未来会发生严重的“文明冲突”。既然可以实证的两个“文化差异”最大的实体尚且如此,其他的“文明冲突”怎么会就没有了解决办法?
作者:秦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