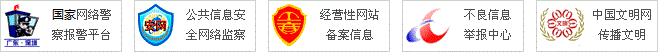另外的坐标系
听戏的孩子,从小是有秘密的。拍着曲子长大,就不知不觉在板眼节拍中调试出独属于自己的另外一种节奏,不急不慌,任世相纵横,自有一段不动声色的理由。
在如今这个以快节奏为主题的社会,我们无法要求昆曲去承担它过去曾经所拥有的辉煌。从现今电影、电视剧、大众传媒所呈现出的这种视听手段来讲,我们没法儿回到昆曲时代的节奏,因为时代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仍然不妨碍我们把昆曲作为一种审美。作为一名教授大众传媒的老师,一个熟知现代叙事手段达到何等发达程度的研究者,昆曲对我人生的影响是为我打开了另外一种坐标系。昆曲,对于今天来讲是一种生活的坐标,它让我们知道人的生活其实有两个层面,外在的层面是生存,内在的层面是生命。我们太多计较外在的生存,忽略了内在的生命。如果我们能让生命更辽阔更舒展的话,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境界。
以大家熟知的《牡丹亭》为例,太守之女杜丽娘长到十六岁才第一次走到自家的后花园,惊异地发现“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那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感叹“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由此,我们可以想到今天的生活,大家都在为生计奔波。比如说许多白领一年四季在一座大楼里上班下班,可能楼后面就有一个小花园或者几棵垂柳,但是人们却无暇顾及。其实,人人心里都掩映着一片园林,无非被一扇无形的门遮挡着。你只要打开一道缝,一眼望去,你便会看到许多以前不曾留意的东西,许多真正契合内心的东西,许多属于梦想的东西。
所以汤显祖感慨“世间岂少梦中人也”?我们这个社会并不缺少做梦的人,其实我们都在做梦,只不过我们没有杜丽娘那么坦率那么勇敢,杜丽娘愿意相信梦是真的,并且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去追随它,然后可以因梦还魂。梦也许在现实中不是一种生产力,不能带来一种物质结果,但是它给我们带来的却是对自己精神世界的一种开掘。今天我们已经远离了一个古典的时代,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种悲悯的情怀和从容做梦的心境。
当我们静下心来欣赏昆曲,就会发现在昆曲中写的生活和今天一定会有某种深刻的关联。有这样一个谚语:山坡上开满了鲜花,在牛羊的眼里都是饲料。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是鲜花太少了么,还是类似牛羊的眼光太多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昆曲主题中的母本包括悠闲的节奏对于我们来讲未尝没有意义。当你听到管弦丝竹起来的时候,多么悠闲,一句道白要多长,那种婉转绵妙的深情,没有一个长度的承载怎么能足够从容呢?
每次听昆曲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自己的心在流水里涤荡一样,终于可以缓慢下来了,在水磨腔里你能感受到光阴是怎么流走的。什么是水磨腔?就像打磨红木家具一样,声腔打磨了岁月,打磨了粗糙而喧嚣的心,而你就可以在中间变得深情,听见春夏秋冬更迭着,和那些很多平时忽略的声音。
以兰花的姿态寂寞生长
昆曲永远不可能回到它鼎盛的时代,但是它会一直存在,我也不认为昆曲这种形式就会死亡。相反,我们看到当下正出现昆曲的复兴。
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用自己的努力让昆曲更好地融进了现代生活。以《牡丹亭》为例,昆曲大义工白先勇先生做了连演三天九个小时全本大戏的“青春版”,东四十条南新仓皇家粮仓推出“厅堂版”,谭盾和上海昆剧团的张军做了“朱家角园林版”,苏州昆曲传奇所里还有“实景版”的只演一折的《游园惊梦》。事实上现在大家都在做《牡丹亭》,我看见的都已经不下十几个版本。而且甚至救活了一些老戏。2010年为纪念清初文人李渔诞辰400周年,被雪藏了350年的“佳人爱慕佳人”的传奇故事《怜香伴》被搬上舞台。这部戏因关锦鹏、汪世瑜、李银河等的跨界合作而轰动一时,几乎场场爆满。
此外,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学生喜欢昆曲,在他们身上一下子就看到了当年我拍曲子的情形。我们不必说昆曲就是最好的,让所有人都去喜欢它也是不现实的。但也不必悲伤,昆曲传到今天,如果没有以前的规模它就会灭亡在我们的手里,我想它会活着,以一种寂寞的方式活着。不是说所有的花儿都要开得像牡丹芍药一样,兰花也是一种生命的姿态。实际上过去一直有以幽兰喻昆曲的说法,昆曲很寂寞但一直生存着,它洋溢着自己的幽香,它在历史的传承中以这样一种不喧嚣的姿态,去传递着自己坚持的品质和风韵,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昆曲之于我,宛如每个清明前必定要啜饮的一盏春茶,宛如每个夜晚来临时或长或短的几笔日记,宛如我随便哪个空闲就可以展开的一段瑜伽,宛如众多熏香中我特别钟爱的薰衣草的那一种气息……我相信自己与昆曲是有缘有份的,而且历久弥珍。这与昆曲是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关,与现在还有多少人听戏无关,甚至与我要不要去振兴它也无关。
对于昆曲,能为其做些什么我并不报有预期。我只能断定我这一辈子都是昆曲的戏迷。我讲过昆曲,写过书,如果以后有必要我还会这么做。(陈娟采访整理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