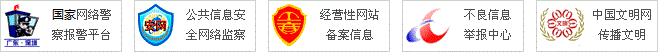南方都市报:从年初到现在,你接连在内地出了三本书:时评集《常识》、艺评集《噪音太多》和日记体散文《我执》,这三本书的写作状态有什么不同吗?
梁文道:当然不一样。时事评论通常是命题作文的东西,你必须根据新近发生的事儿来写作,有时甚至题目都是编辑给定的,因此它不是一种毫无限制的写作。但是,《噪音太多》就是一个比较随性、比较闲适的写作,写作的时候很自由,我不用考虑最近什么电影成为大家的话题,我就有任务去看、去写。至于《我执》,它看起来像日记,其实有一个完整的叙事在里面,当初写的时候是想帮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做一番重新的注解,但是写着写着就跑调了。
南方都市报:有读者认为,你的时评有更多的理性,但是像《我执》这样的文字则会具有更多的感性色彩。
梁文道:也不至于,我觉得我都很稳定。我是一个写任何东西的时候都很理性的人,我不是那种容许自己的文笔去放纵的那种人。我用字很节制,我的字典是很有限的,我很节制自己用字的范围,尽量不用僻字、生字,我的表达也是尽量约束自己,越简洁、越可读越好。当你这么约束自己的时候,你的写法是很冷静的。但是会不会永远都很理性呢?不是。恰恰相反,感性很重要。写时事评论是需要感性的,很多人以为写评论不需要感性,其实非常需要感性,因为我需要同情地投入我的那些对象。
南方都市报:就我所知,你的《常识》进入了很多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而正如你所说,时评应该是一种速朽的文章,对此你怎么看?
梁文道:我觉得有几点。第一,《常识》这本书赶上了时评热,早几年或晚几年出可能就不一样了。这几年各地报纸都流行办时评版,时评也越来越受关注,它赶上了这个热潮。第二就是我写时评的方法很少就事论事,而是就一件事去讨论我们常见的一些观念及上面纠结的地方,因此也就比较容易超出一时一地的时空限制。第三,就像我在序言中所说的,这是“江山不幸诗家幸”,我们的确有太多的东西在重复着,比如说矿难,你敢说以后几年不会再有矿难吗?坦白讲,我不相信。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江山不幸”,你写的东西不容易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