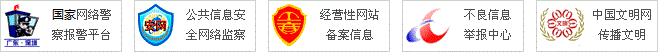本报记者 苏莉鹏
再过几天,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将迎来73周岁的生日,他为自己许下了一个愿望,希望这一年能回归他的老本行——写作。
这几年,他为保护传统村落四处奔走,发起“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项目。截至目前,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完成村落数目已逾百个,分布于中国各个省份。冯骥才先生为传统村落留住“乡愁”花费的心血有了初步的成效。
即便为保护传统村落花费很多的心力,冯先生依然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今年年初,他的6部新作出版,涵盖了文化游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艺术品收藏、散文小品、纪实文学等多方面内容。其中,《泰山挑山工纪事》是最引人关注的一本。
《挑山工》,这篇冯骥才先生写于1981年的散文,1983年起收入小学语文教材,成为几亿人熟知的经典美文。冯骥才先生也因为这篇文章成为泰安市荣誉市民。几年前,当他得知泰山的挑山工已经是最后一批、面临消失的消息后,便想再去拜访泰山挑山工。终于在2013年年底成行,并为泰山的挑山工做了口述史,于是便有了《泰山挑山工纪事》一书。
“虽然我和他们不曾交流,甚至由于他们低头挑货行路,无法看清他们的模样,但是他们留在了我的心里,成为我写《挑山工》的缘起”
再写挑山工,不但实现了冯先生的一个心愿,也唤起了当年拿着语文课本、被挑山工精神鼓舞的人们的情怀。初登泰山,冯先生是个20岁出头、意气风发的青年,在那里,他偶遇挑山工。而今再登泰山,年逾七十的他只为挑山工而来。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寻访挑山工的经历,如同挑山工肩上刻满岁月伤痕的扁担,在冯先生的心中抹不掉、化不开。
1964年,22岁的冯骥才在画家溥佐先生那里学画,有一天,溥佐先生对他的几位学生说:“跟我去泰山写生吗?”冯骥才兴奋难抑,立刻呼应前往,临行前的几天,他兴奋得夜里睡不着觉。“泰山对我有种天生的魅力,这可能来自姥姥那里。姥姥家在济宁,外祖父在京做武官,解甲后还乡,泰山是经常去游玩的地方。姥姥常对我讲泰山的景物和传说。”冯先生说。也许是这份早就根植于心中的情愫,让他第一次去泰山时,就走进了姥姥讲过的泰山故事里,也沉醉在那层层叠叠的美景中。“那时没有相机,我掏出小本子东画西画,没有钱,只能在山脚下买些煮鸡蛋和大饼塞进背包,带到山上吃。我还记得坐在经石峪的石头上,一边吃大饼卷鸡蛋,一边趴下来喝着冰凉的溪水,一边看着那些刻在石头上巨大而神奇的字。还记得一脚踩空,掉到一个很大的草木丛生的石头缝里,半天才爬出来。”冯先生回忆说。
就在那次因写生登岱的过程中,冯骥才遇见了挑山工。他看到那些挑山工,都是一个人,全凭肩膀和腰腿的力气,再加一根扁担,挑上百斤的货物,从山底登着高高的台阶,一直挑到高入云端的山顶,“虽然我和他们不曾交流,甚至由于他们低头挑货行路,无法看清他们的模样,但是他们留在了我的心里,成为我写《挑山工》的缘起。”
散文《挑山工》里的见闻,多来自1976年第二次登泰山,“《挑山工》中那个黑黝黝、穿红背心的汉子,就是这次在山里遇到的”
冯骥才先生写进散文《挑山工》里的见闻,多来自1976年第二次登泰山。那一年他在天津工艺美术工人大学教书,有一次他和另一位老师决定带学生去山东上写生课。那位老师先带学生去菏泽上写生花卉课,冯先生则独自到泰山采景,等候学生来上写生山水课。那时山上没有电话,他与菏泽方面的师生联系只能依靠信件。信写好,托付给挑山工带下去,扔进泰安的邮筒,那边来信,再由挑山工带上来。由此,他便与挑山工有了进一步接触。
“这些汉子虽然大多沉默寡言,却如这大山一样纯朴、真实、踏实和可信。在他们几乎永远重复着的吃力动作中,我读出一种持久、坚韧与非凡的意志。后来我写散文《挑山工》中那个黑黝黝、穿红背心的汉子,就是这次在山里遇到的。比起别的挑山工,他好像稍稍活泼一些,与我有一些无言的交流,也给我一种唯有挑山工才能给予的启示。”冯先生说。
那次在泰山,冯先生还遇到了一个女挑山工。他们在泰山中天门相遇,冯先生的背包里塞进了他捡到的好多泰山石。女挑山工便问他要不要挑,冯骥才说你挑不动,女挑山工笑了笑便把背包行囊挑起来。“到了火车站,她把我的东西撂在地上,用毛巾擦汗,她只要我4角钱,我说包里有石头太重了要给她5角,她笑着说知道是石头。”
多年后,冯先生在《挑山工》中这样写道:你来游山,一路上观赏着山道两旁的奇峰异石,巉岩绝壁,心情喜悦,步子兴冲冲。可是当你走过这些肩挑重物的挑山工的身旁时,你会禁不住用一种同情的目光,注视他们一眼。你会因为自己无负载而倍觉轻松,反过来,又为他们感到吃力和劳苦,心中生出一种负疚似的情感……
2013年,冯先生寻访“最后一代挑山工”,“我心中有一种忧虑和苍凉感,这正是这些年来那种抢救中华文化常有的情感,竟然已经落到挑山工的身上”
写完《挑山工》后,冯骥才又去过两次泰山。一次是1989年陪母亲前去,那次登山他发现,他写的《挑山工》产生了效应。在上山的路上,他多次见到一些小学生与挑山工合影,孩子们看挑山工的眼神不是好奇,而是敬佩。另一次是1996年,泰安市政府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
那之后,冯先生便开始投入到城市历史保护和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中,经年累月各地奔忙,无暇再去登泰山,但挑山工的影子并没有在他心中淡漠。“有一次听到一个说法,说现在是最后一代挑山工了,怎么会是‘最后一代’?时代变化得太剧烈了,连挑山工都‘濒危’了。我想,我该抓紧时间专门去泰山访一访挑山工了。”
2013年11月,冯先生第5次登上泰山,这一次他为的是寻访“最后一代挑山工”。沿途的景色依然如故,但他更留意的是挑山工的状况,“这一次上山,竟然没看见一位挑山工,不知道是他们晌后收工了,还是真的已然日渐稀少。我心中有一种忧虑和苍凉感,这正是这些年来那种抢救中华文化常有的情感,竟然已经落到挑山工的身上。”
那一次,他与老挑山工和中年挑山工座谈聊天,并为他们做了口述史。他还到挑山工的驻地,了解了当今挑山工的一些生活状况。冯先生说,做口述的目的,是因为历史上关于泰山挑山工没有专文记载,可是挑山工一直是泰山特有的一种人,也是一种生活和人文,“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历史应当厘清,现实应当面对。”
冯先生探访了位于泰山中天门一带的挑山工居住的简易工棚,挑山工的真实生活令他感到震惊,“那间挑山工吃饭的小屋惨不忍睹,用一些石头砖块和木板架起来的条凳和小桌,堆满吃喝用的饭盆、水瓶,四周是垃圾一般的木箱、草筐、纸箱和杂物。一些装在各种袋子里的煎饼、馒头、菜,杂乱不堪地挂在低矮的房梁上,可能是为了防止鼠类偷吃。这便是挑山工干完活儿回来喘息一下、填饱肚子的地方。”冯先生说他看到这个场景心里特别不落忍,“觉得我们城里生活那么好,自己所敬佩的挑山工的生活竟是这样,心里难过。”他嘱咐挑山工队伍的队长至少可以先实际改善一下他们吃饭、休息的条件,“无论历史还是今天,泰山有这样美好的人文,挑山工是有功的。我们要爱惜他们,不能对不起他们,更何况他们可能是最后一批挑山工,不能叫他们最后被穷困逼出历史舞台。”
本组撰文 本报记者 苏莉鹏
图片由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