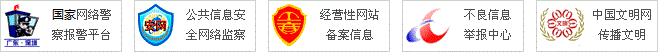19世纪20年代,外国商团在跑马厅阅兵日。
1862年6月2日,雨后的暑阴中,一艘奇特的西洋式三桅帆船驶入了上海吴淞口,它的前樯插荷兰三色旗,中樯插英吉利米字旗,后樯则插日本太阳旗,这便是日本明治维新前夜,日本幕府打破二百年的锁国体制后,第一次派遣来华的“千岁丸”。船上的51个日本人中,除了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高杉晋作留下了《游清五录》以外,其他人则有名仓予何人的《官船千岁丸海外日录》、《支那见闻录》;中牟田仓之助的《上海行日记》、《上海滞在中杂录》;松田屋伴吉的《唐国渡海日记》;随团医师尾本公同的从仆峰源藏,又名峰洁的《航海日录》、《清国上海见闻录》等共17篇文字留传了下来,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上海的状况提供了不少详细资料。因为“千岁丸”是刚从英国人手里购置的二手货,驾驶的人仍然是英国人,所以船上还有船长亨利.理查多松等英国人15名;又因日本当时与清朝尚未建立正式商贸关系,所携货物需以荷兰商品名义方能进入上海,所以还有一名荷兰商人图莫林古。他们停泊的地点是法租界的荷兰领事馆点耶洋行处,入宿附近一家由中国人张叙秀经营的洋式宏记旅馆。按照名仓的记述,宏记以北不远处就是清廷税关建筑:“江南海关”。
此时太平军占领了苏州,正在攻打上海,根据《北华捷报》的统计,当年上海市区人口骤增到了300万,其中250万是难民。而《吴煦档案选编》1862年统计是:一年内死亡的人数竟然不下百万。名仓予何人说道:“出薛家,过江边,见有逃难携妻子住于船中者,其舟不知有几千百艘。”江上、租借和上海城里也到处挤满了难民。其结果正如峰洁所说:上海城内“粪芥满路,泥土埋足,臭气穿鼻,其污秽不可言状。”纳富介次郎又说:当地人把死猫烂狗、死马死猪死羊之类以及所有的脏东西都扔入江中,这些都漂浮到岸边。再加上数万条船舶上的屎尿使江水变得更脏。而且“江上还时常漂人的尸体。当时霍乱流行,难民等得不到治疗,很多人死于饥渴,也许因无法安葬而将其投到江中。此景真是目不忍睹。”而当时的饮用水就是江水,加一些明矾沉淀一下而已,于是他们随行来的仆从硕太郎、传次郎,炊夫兵吉的尸体,就被埋葬在浦东烂泥渡。高杉晋作对此的态度是:“闻同行渡边与八郎从仆昨夜来急病,今朝冥行云。同行者病客甚多,诸子畏缩,有或促归思者。予以为,一步出国死已决矣,然空死无益,唯身自护吾体无他也。”
四方难民的群集,自然带来了米价腾贵,名仓予何人说:“余至米铺,寻常米价大抵铜钱八十文至九十五文,而现今定价十倍云。”峰洁也与一阁寄居小舟的难民马铨有一段笔谈:“问曰:‘今此江中之人,皆何处人乎?’铨曰:‘此系苏州难民矣。’洁曰:‘大概有几人?’铨曰:‘难细言,约十万余人。’洁曰:‘此十万人,所食米盐皆买于上海市乎?’曰:‘然矣。’曰:‘费价日当腾涌矣。’曰:‘一石米价常日三四千钱,今则九千钱矣。’洁曰:‘钱尽将如何?’曰:‘无可如何。’”6月5日,纳富介次郎记述了和荷兰、法国领事一同去拜会上海道吴煦的全过程,名仓更是一方面描绘道台衙门的排场和堂皇;一方面也描写了在这冠冕堂皇的排场下面,处处显露出的衰败。纳富和峰洁都有:道台不仅令不行,官衙内乱晒旧衣。而且招待客人的点心和水酒一撤下,即被衙役们毫不掩饰地分食一空!衙役也受米价的拖累,人都快饿死了,哪能还要求他们体面?
高杉记录了一段在如此积贫积弱的乱象中,与中国士人温忠彦的一段笔谈:高杉:“请问,宋朱文公所说格物穷理,与西洋人之所说穷者异否?”温忠彦:“朱文公之格物穷理,即圣人之齐家修身,推进一层,不外乎诚之一字,贵乎实践,不取恥深。至西人所讲,虽本乎理茅,近于术数,未免尚隔一层尘埃。此论虽僻,鄙见如此,请教。”高杉:“为义为利天地隔绝,不待言论而明,然治天下齐一家,内自诚心诚意功夫,外以至航海炮术器械等,尽不言穷其至理,则不能治天下也,不能齐一家也。不能穷航海炮树之等之理,则所以诚心诚意功夫不至也。故以所为利之器械为义是用,乃取舍折中之道也。不然则口虽唱圣人之言,身已为夷狄之所奴仆矣。”温忠彦:“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天下之本源,浅而约之,则诚正,推而致之则治平,道贯古今,理周中外,至航海炮术等事不过格物之一端,圣人治天下以仁,不得已用兵,戢暴,正所以全仁了。然否?”这虽然是一个国士和一个庸徒不对等的对话,但他们被圣人、朱熹阉割了思想而不自觉,面对强盗还要大谈诚和仁,正是昏聩得让人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