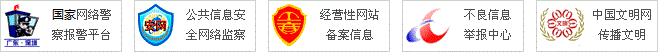当下文学理论的困局与出路
吴子林:您觉得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存在什么问题?有什么样的对策?
童庆炳:长期以来,文学理论研究常被说成比较“空”,“空洞无物”,“不及物”,或“大而无当”,人们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是目前中国文学理论的困局。这种困局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经常置于认识论的框架内,常常变成概念与术语的游戏。认识论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是重要的,对于自然和社会科学是很有用的,但对于美和艺术的这类特别富于人文情感的事物的复杂情况,往往缺乏解释力。认识论只能解决文学中的认识问题,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认识论的框架,无非是一系列的二元对峙:现象与本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个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偶然与必然、有限与无限等,它们很难切入文学艺术和美的复杂问题中,很难解决艺术与美的问题。如对文学的本质、文学的真实、文学的典型等许多问题,都无法用这些二元对峙的概念去解决。这是被事实所证明了的。因此,抽象的哲学认识论常常不利于文学问题的具体解释。但是,文学、文学理论与历史的关系则有着深厚的联系。任何一个文学问题都是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针对一定的现象提出来的,我们的研究就必须放回到一定的历史语境中才能得到具体的解释。因此,可以说,无论文学问题的提出,还是文学问题的解答,都与历史语境相关。离开历史语境,孤立地运用概念进行逻辑的推理,不但显得空洞,而且解释不了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理论首先是求真,真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如何去讲求善与美呢?所以我反复强调,文学理论的力量就在于对历史语境的把握。“论从史出”是我的一贯主张。我多年前就在批判所谓“新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和作品中,提出“历史—人文张力”说,并把它运用于各种作品的解释中,就是一种立足于现实的文学创作的理论,其解释力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由此,我觉得我们的理论要有一种伟大的历史感,这才可能是真正的有力量的理论。归结起来,当前文学理论的困局的出路有二:一是文学理论应面对现实,并与当代的文学创作、文学现象保持密切和生动联系,只有认真去研究和解决从中国的现实里面提炼出来的真问题,做深入的细致的探讨,才可能有真学问;二是做到前面说的“历史语境化”,对文学理论问题放回到原有的历史语境中去把握,作一种溯源式的具体化历史研究。
吴子林:近年来,不时有“反对理论”或“理论已死”的论调,对此您怎么看?
童庆炳: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我不同意“反对理论”或“理论已死”的论调。理论创造是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它是对一个事物深层次的、本性之物的理解与把握,理论的抽象有助于我们摆脱无知、半无知的状态。文学理论不是文学创作的附庸,它是文学理论家与作家一道面对生活的发言,是在一定现实生存境况下的探索,它有着思想的力量。即便只是面对作品发言,作为“不断运动的美学”,文艺批评也有它独立的价值。文艺批评的根基既不在政治,也不在创作,而在生活、时代本身。生活、时代既是创作的根基,也是批评的根基。创作与批评的根基是同一的。优秀批评家应该根据自己对生活与时代的理解,对作品作出自己的独特的评判,或者借作品的一端直接对社会文本说话。这样,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如何来理解现实与时代,想对现实与时代发出怎样的声音,就成为他的批评赖以生存的源泉。创作与批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也不存在谁依靠谁的问题。但它们合作,共同产生意义。批评家创造的世界与作家、艺术家所创造的世界是同样重要的。袁枚就说过:“作诗者以诗传,说诗者以说传。传者传其说之是,而不必尽合于作者也。”
吴子林:正如伽达默尔所揭示的,“理论的原初意义是真正地参与一个事件,真正地出席现场”。现在某些“理论家”从生活事件之中抽身出来,已然遗忘了理论的这一原初本义了。未来的文学理论研究前景将会怎样?
童庆炳:我认为,未来的文学理论与纯文学一起边缘化是很正常的事情,文学和文学理论做什么“时代的风雨表”,究竟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我一直认为,当经济和社会问题成为时代的中心,是社会正常的发展。把文艺当成中心是非正常的危险的现象。在文学理论边缘化的情况下,我们讲潜心研究文学理论和批评自身领域的问题,那时,文学理论和批评将变得更加学理化、专业化和学科化,而不断向深度拓进。在与现实文艺发展的密切生动的联系中,在进入历史语境的深度把握中,在发扬文学理论批判精神中,形成一种深厚的学术力量。真正的文学理论不会与世俗的商业力量同流合污,而独立走向自己的未来。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地摆脱困局,不断地纠正我们的航向,是十分必要的。(吴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