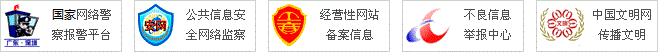溥仪为什么没有相中漂亮的年轻小姐呢?后来他和我谈过这件事,他说:“我喜欢朴朴实实的人,但她给我的印象中不够稳重,恐怕很难和我生活到一块儿,她也不可能真心爱我的。”
溥仪在前井胡同五妹韫馨家居住期间,许多亲属以及与其前半生有过种种瓜葛的人纷纷前来看望。溥仪后来对我说,最令他为难的是,有些人仍把他当做“皇上”对待。
第一个到前井胡同韫馨家看望溥仪的旧日随侍就是赵荫茂,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就入宫伺候溥仪了,在溥仪身边二十多年,直到“皇上”当了苏军的俘虏。其间,他受到赤严酷的惩处,也得到过丰厚的赏赐,据说仅用溥仪的一笔赏钱就在北京盖起一栋小楼,便设龛供俸溥仪的照片,感念“皇上”的恩德。他依靠在膳房给“皇上”烧菜的本领,又当上某机关招待所的厨师。
赵荫茂见了溥仪激动万分,一面呼唤“皇上”,一面磕头不止,溥仪照例扶起他来,颇为生气地说:“我已是公民,直呼姓名有何不可!”那天,溥仪还留赵荫茂一起吃饭,详细询问分别后的经历,临别还嘱咐说,下次见面相互要以同志相称。我和溥仪结婚以后赵荫茂还来过几次,溥仪也到赵家去过,赵荫茂的元配妻子去世后,溥仪还曾说服赵家子女帮助赵荫茂实现了再婚的愿望,这一对儿历史上的主仆,今天成了“同志”。
自1959年12月23日起,溥仪遵照北京市民政局的安排,离开了五妹家,搬到东单附近苏州胡同南口崇内旅馆,与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和郑庭笈等人住在一起,又过上以参观学习为内容的集体生活。
有一天,溥仪正在崇内旅馆的房间休息,服务员敲门进来,告诉他说有两位老先生在楼下求见。溥仪接过服务员手中的信封拆开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这是两张向“皇上”“请安”的红帖。恭恭敬敬的墨笔正楷字写在木红纸上,一个落款赫然是“前清翰林院编修陈云诰”,另一个则是“前清度支部主事孙忠亮”。可是仍然称呼溥仪为“皇上”并且愿意给他磕头的人,不仅有皇亲以及贴身数十载的随侍,还有已经灭亡了48个年头的“大清王朝”的遗臣!一股怒火在溥仪的胸中燃烧,他厌恶这些遗老们;不愿见他们,就对服务员说:“麻烦你们转告来客,就说我不在。”于是服务员替他挡了驾。
这件事第二天就传到周恩来耳朵里,总理加以认真的思考,结论是:人的思想不容易改造!他说,如果不把溥仪特赦出来,谁会相信还会有这种人,皇帝经过改造都不想当皇帝了,而过去的臣子却还没有忘记这个皇帝,还想当臣子1960年1月26日周恩来接见溥仪和他的亲属时说:“现在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把你当成平民看待,可能有的人还会向你下跪打躬。”溥仪当时就告诉总理说:“这次回来后,还有两个老头拿着用清朝官名写的信来见我,当时我说要出门,没空儿,没有见他们。我想是没有办法说服他们的。”
在短短的时间里,溥仪碰到了那么多来磕头的人,不免悲观。然而,总理并不赞成他的认识,要求他面对“社会死角”,不但自己不受影响,战胜环境,还要帮助落后,这些话被溥仪记住了。
一两天后,族侄毓遑又到韫馨家向溥仪行三拜九叩大礼来了。毓也是五爷府的后人、大阿哥溥镌的胞侄,当时在德胜门煤厂当业务员,没想到把溥仪给惹生气了,从此再不敢见溥仪的面。
溥仪特赦后的第一个春节过去以后,心怀旧礼的人并没有绝迹,溥仪到植物园以后,同类事又一而再地发生。
有一次,溥仪在由植物园回城里的路上,遇见一位原来宫中的殿上太监。这位当年伺候过小皇上的老人,因为已听说“万岁爷”特赦回到北京的事儿,所以一眼便认出了溥仪,并恭谨地向皇上请安。虽说没有像过去那样就地三拜九叩,可那谦卑的样子已足使路人侧目并为之惊奇了。溥仪紧忙过去搀扶老人,诚恳地解释说:“从前的溥仪已经死了,现在我是公民,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这次溥仪没有像在祟内旅馆那样大动肝火,除了尊重老人的心理之外,不能不说是在学习中得到了进步,对社会上客观存在的各种阶级现象有了一些认识。
1960年7月的一个星期日,溥仪进城到五妹家度假。五妹告诉他,前几天有位姓陈的女同志送来一大包东西,有香皂、牙膏等生活日用品,还有两瓶酒、一匣糖以及其他许多食品。来人说,是父亲陈懋侗让她送来的。
陈懋侗就是溥仪青少年时代最敬重又最依赖的“帝师”陈宝琛之子,他也曾随溥仪到长春;先后出任“执政府内务处事务官”、“宫内府内务处需用科长”、“宫内府侍卫处处长”等职。
现在,20世纪的60年工,陈懋侗又给溥仪送礼品来了。这礼品之中,显然包含着二三十年代他父亲对溥仪的感情,也显然包含着三四十年代他自己对溥仪的感情。溥仪反复考虑结果,认为不该收这份念旧情的礼品,于是决定只留下糖果,其余送回。
8月7日那天溥仪抽暇去陈家退礼。因为路不熟,他找了两个伴儿同行,一个是族侄毓,另一个是乳母的孙女王佩英。这次去,溥仪是决心要帮助一下陈懋侗的。三个人按照门牌找到陈家。陈懋侗看见溥仪后,脸上现出惊喜之色,继而又进来一男一女,还带着他让女儿送去的包裹,遂又疑惑起来,不知应以何礼接待。溥仪抢先伸出手来,陈懋侗勉强握了一下,显得很拘谨,半天说不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