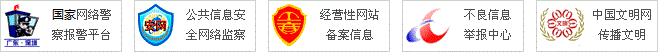嘉道以来经世思潮之得以勃兴,其原因颇为复杂。自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问世以后,今文经学对晚清思想的影响便被特别突显出来,仿佛只有梁氏所谓“以经术作政论”的今文经学才是当时经世思潮勃兴的唯一思想理论基础,大有将两者划上等号之势。这种认识与历史的本相颇有距离。其实,今文经学诚然是嘉道以来经世思潮勃兴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但绝对不是唯一的来源。乾嘉汉学、程朱理学、浙东史学、桐城派古文学,等等,有多种传统学术流派为之提供了思想资源。可以说,嘉道以来的经世思想能够勃发成为一种时代思潮,正是中国本土思想传统从多方面回应时代“变局”挑战的必然结果。
(一)乾嘉汉学
嘉道以来经世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乾嘉汉学末流流弊的批评,即抨击烦琐虚空的考据学,倡导对现实社会与民生的关怀。其实,这种批评不仅来自汉学以外的其他多种学术流派,而且来自汉学的内部,是汉学家经世意识的激发涌动。
明末清初,汉学的开山祖顾炎武针对王学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曾经提出了一个“经学即理学”的重要命题。这个命题蕴涵的意义有二:其一,理存在于经中,治经所以明道。其二,治经只是明道的手段,明道的目的在于经世。可见,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命题包含了实证的考据学与实用的经世学思想,而这二者又是密切相关联的。毋庸讳言,乾嘉汉学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走了纯粹考据学的偏锋,不少汉学家失去了经世精神。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清朝统治者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这是一般学者所难以抗拒的严酷现实。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由顾炎武开创的经世之学,即使在乾嘉汉学鼎盛时期,也并未完全中绝。学界公认的汉学集大成者戴震“抱经世之才,其论治以富民为本”,他深刻地揭露了“以理杀人”的黑暗现实。经学家王念孙敢于抗疏弹劾和珅。号称汉学护法的毕沅、阮元均是经世派的封疆大吏。汉学家对现实与民生关怀的精神是不容否认的。
更有甚者,在嘉道以来批判汉学思潮中,有不少来自汉学营垒内部的声音。扬州学派的汪中、焦循、凌廷堪可谓典型。扬州学派的兴起,是对吴、皖二派的补偏救弊。具体而言,扬州学派的“通学”,不仅能纠正吴派盲目崇汉之“固”和皖派为考据而考据之“偏”,而且能发掘出经世大义,使乾嘉汉学由实证的考据学转到实用的经世学的新路向。汪中为学不尚墨守,反对汉学末流的门户之见与烦琐考据,而惟求通经致用。焦循甚至不承认“考据”之为学,他否定考据名目,为学主张汇通,治经在于明道,以求立身经世。凌廷堪对汉学流弊的批评更是击中要害,指明汉学家不通古今之变,为学不通世务,不切时用,完全钻在故纸堆中,失却了经世的意义。这些表明乾嘉汉学家尤其是扬州学派的学者,也能因应世变,为嘉道以来经世思潮的勃兴注入思想活力。
(二)浙东史学
浙东史学的鼻祖黄宗羲,在强调“经术所以经世”的同时,特别重视“读史”与“证明于史籍”,以开浙东学术“史学经世”的先河。黄宗羲上承王阳明、刘宗周的心学,下启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的史学,其间经世精神一脉相承,而尤以章学诚为典型。
章学诚是乾嘉时期与汉学大师戴震同时代的浙东史学大师。他的著名的“六经皆史”的命题,一方面是针对汉学家空言著述的流弊而发的。他从根本上否定汉学家由音韵、文字、训诂的考据学以明经达道的治学路径。在他看来,当时的汉学家将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命题抽掉其明道经世的意义,而走上训诂考订的偏锋。对古代经典的研究忽视其思想内容的探讨,只注重经典形式的研究,使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得到大力的发展。汉学家们尽管可以著作等身,但并未明经达道。另一方面则蕴涵着“史学经世”的意义。在章学诚看来,史学的研究就是要从作为“先王之政典”的六经之类的典籍中,发掘出先圣先王治国平天下的经世精神,从历史上总结并吸取经验教训,以为现实政治服务。因此,章学诚反对汉学家脱离现实的为考据而考据的纯经典研究,主张研究经典的意义在于致用于现实,尤其不能死守经说,而要因时变通。
可见,浙东史学的经世思想也为嘉道以来经世思潮的勃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事实上,嘉道以来边疆史地学与域外史地学的勃然兴起,其根本的动因与直接的目的都在于经世,这是史学经世精神的一个典型例证。
(三)桐城派古文学
以姚鼐为首的桐城文派形成的乾隆时期,正是汉学大盛、如日中天之时,学术思想界扬汉排宋的风气盛行。桐城派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的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流行的汉学相抗衡。桐城派与汉学相争固然有其学派之间的门户之见,但在乾嘉汉学衰落、流弊百出之时而涌现的批判汉学思潮中,桐城派当然也不能置身事外,其所作所为只不过是此种社会思潮的一片波澜,因此,毋宁说是其经世精神的体现。姚鼐少时即有经世之志。他对汉学的攻击,固然或有发泄私愤之意,其实更与他的论学宗旨及经世精神相一致。姚鼐批判汉学的精神由其弟子方东树发挥到极致。方东树著《汉学商兑》,对乾嘉汉学作了总结性的批判:一方面,指责汉学家标立门户、扬汉抑宋之害;另一方面,抨击汉学家钻在故纸堆中,严重脱离实际,汉学支离琐碎,与国计民生无关,虽实而虚。这便将嘉道以来批判汉学思潮推向顶峰。
嘉道以来的桐城派学者不少即是经世派的代表人物。如姚莹,他的经世思想,不仅表现在关怀国计民生,揭露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而且表现出反帝爱国、开眼看世界、甚至向西方学习的新的时代内容。鸦片战争时期姚莹在台湾抗击英国侵略者的行为,以及他的《康輶纪行》一书关注世界的经世精神,表明姚莹是随着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所开启的由经世而学西方的这股潮流不断前进的一个突出的代表。可见,嘉道以降,随着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日益加深,桐城古文派的经世精神也日愈强化。
(四)程朱理学
唐鉴开启了晚清理学复兴的新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提倡理学的复兴是要“守道救时”。关于“守道”,唐鉴著《国朝学案小识》,编制出一个严密的程朱理学道统传承体系,要“守”的就是这个承接孔孟的程朱理学道统。所谓“救时”,即经世。唐鉴的门徒倭仁与曾国藩一为“守道”的主将,一为“救时”的典型;是他们共同高举了理学复兴的大旗。
倭仁是理学修身派的代表,是理学的正统派。所谓正统的程朱理学,主要是一种道德实践哲学。倭仁不仅自己注重道德心性修养,踏实做圣贤工夫,努力完善自己的道德理想人格;而且在社会上大力提倡,希望将社会上的人个个造就成儒家“君子”。以倭仁为代表的理学修身派仍然坚信儒学的现世价值,其经世方略完全没有超出传统儒家道德论的范畴。曾国藩是理学经世派的代表,他很重视“经济之学”,大大发扬了唐鉴提倡的“救时”之旨。所谓“经济之学”,即是经世之学。以曾国藩为首的理学经世派,更加关注现实社会,提倡务实的精神,能对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作出较为积极的回应。他说:“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因此,在回应嘉道以来的内忧外患的社会“大变局”时,他们不但能充分发挥儒家传统的经世精神,力挽狂澜于既倒;而且能部分地或有限度地吸收接纳西学,进而举办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使中国社会开始迈上近代化道路。
总之,乾嘉汉学、浙东史学、桐城派古文学、程朱理学与今文经学一样,都为嘉道以来经世思潮的勃兴提供了思想资料。也就是说,嘉道以来经世思潮勃兴的传统思想资源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今文经学。当然,这些只是儒学内部的几个重要学术流派。事实上,在乾嘉汉学衰落之时,除了今文经学与程朱理学的复兴之外,还有陆王心学与诸子学的复兴,均为经世思潮提供了精神养料。甚至佛学与道教思想,在晚清也有向“入世”转向的趋势。所谓经世派,极少纯粹书斋式的学者,而一般都是介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也并不是单一的,而大都是从传统思想中吸取了多种有用的成分。尽管他们同以经世为依归,但是各自的经世思想体系都是非常庞杂的。
作者:李细珠